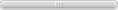好的“讲述者”与优秀“造梦师”——国外电影编剧一瞥
日前,好莱坞著名编剧弗兰克·皮尔森在家中安详去世,享年87岁。这位才华横溢的编剧,曾多次获得奥斯卡、艾美奖提名,他的作品极具戏剧张力和艺术魅力,为好莱坞电影增添了不少光彩。在全世界影迷追忆皮尔森的时候,处于失落世界里的电影编剧的命运再次让人感慨。他们在狭小幽暗寂静的空间里冥想、码字,时而寂寞抓狂,时而自言自语,成为银幕的“造梦师”。
“观照现实”和“塑造梦想”,是编剧艺术的核心。随着电影艺术发展,电影产业化加深,观众的观赏趣味和审美需求都在不断地提升,所以对编剧的要求就变得更加迫切。好的编剧既要全身心投入,又要能冷静抽离;要能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,还要擅长分析观众的心理、情感需求,才能制造出打动观众的“梦境”。
讲述者 观照现实
“人类如果没有故事,就没有智慧、快乐和希望”,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《一千零一夜》给我们的启示。做一个好的讲述者,是编剧的首要任务。
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成为讲述者的素材,大到一个历史事件、传奇人物,小到一个情感关系、一段对话。“讲述”不只是交代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还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和动人心魄的创造力。
以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为例,影片编剧彼得·斯通在这部影片中讲了两个故事,一个取材于现实,无比冷峻残酷的“灾难故事”,一个生发于幻想、浪漫凄美的“爱情故事”。正是两个故事、两种色调、两股力量的交织融合,才让这部作品既有令人惊心动魄、摧心伤肝的人世痛苦,又有能让人感受到纯净唯美、浓烈炽热的爱情力量。
相比较《泰坦尼克号》的大开大阖,《通天塔》的情节跌宕。《通天塔》曾获得过金球奖最佳剧情片,通过对三个现实故事的讲述,交织成一个充满戏剧性又极具批判和反思的作品。
这三个事件当中,第一个关乎情感,是人们普遍关注的“中年危机”问题,第二则涉及了种族歧视、贫富差距和个人尊严的问题,而第三件事情的关注焦点则是有性变态倾向的问题少年。剧作者没有针对每个问题直接给出自己的态度,而是让三个发生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事件,因为一个意外的巧合,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,然后彼此交错,最终让他们产生不同的体悟。
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,对于观众、对于社会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。有些被现实分开的情侣,被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故事鼓励,重新燃起了对抗现实、把握爱情的勇气。被《通天塔》指引,有些不婚主义者也重新感叹人生苦短、相守可贵,走上了婚姻的殿堂。
好的讲述者,可以驱散人的寂寞,可以给人以共鸣;好的讲述者,可以让故事带给你对待生活的另一种态度,故事里所写的彼端截然不同的风景会让你发现生活的不同样貌。
造梦师 创造奇迹
从乔治·梅里爱《月球旅行记》问世以来,电影人就开始尝试扮演“造梦师”的角色。尤其在电影技术和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,剧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老老实实讲述现实故事,而是要将臆想、疯癫、长梦揉成一个色彩缤纷的球,让它绽开绮丽的烟火。
大卫·林奇自编自导的电影《穆赫兰道》在剧作处理上借鉴了弗洛伊德的“精神分析法”,将哲学著作《梦的解析》当中很多理论研究通过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,构成了一部情节诡谲、支离破碎却又隐含玄机、疯狂迷乱的梦。
这部电影分为两个时空,一个梦境时空,一个现实时空。梦境时空讲述了女孩贝蒂只身来好莱坞发展,遭遇了一个落难女孩丽塔。贝蒂事业如日中天,又遇真命天子,而丽塔却丢失了记忆,忘记了来路。贝蒂与丽塔情同知己,倾其所能帮她寻找希望。梦境的故事看似顺理成章,符合常情。贝蒂阳光热情,简直是天使的化身。然而在影片的后半段,剧作者重回现实,将前半部分所有的美好一点点揭开毁掉。其实在现实时空中,贝蒂和丽塔是一对同性恋情侣,丽塔是小有名气的女演员,而贝蒂却是个千年不变的大龙套,贝蒂因为发现丽塔和一个男导演暧昧不清,于是醋意大发,买凶杀了丽塔,那个梦境时空正是贝蒂在买凶杀人之后的心理映射。片中有很多线索似的道具,比如骨灰盒的蓝色“钥匙”代表悔恨,比如卧室里的油漆代表偷情和不道德的性,比如死尸代表对自我的唾弃和憎恶。就如同弗洛伊德说的,梦是人内心情感欲望的外化,一切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在梦里都会得到满足。影片用梦境代替现实,用意识代替想象,用丰富的电影符号和象征意义代替剧情,诡异而华丽,给人感官上的刺激、心灵上的震动。
与大卫·林奇一样,伍迪·艾伦也是一代鬼才,他的编剧才华尤甚于导演才能。他的新作《午夜巴黎》剧本上天马行空的创意,让整部电影充满了灵动的色彩,满足了大批文艺爱好者一个怀旧的美梦。《午夜巴黎》讲了一个灵感枯竭的小说家,在巴黎街头买醉,突然一辆马车停在了他的身边,车上的旅人热情地邀请他上车,而下车后他才发现自己竟然置身于心中向往的巴黎黄金时代。在这样一个神奇而迷人的夜晚,他邂逅了许多自己膜拜的历史文化名人,先后同海明威喝过酒,和菲茨·杰拉德谈过心,跟斯坦因跳过舞,调戏过毕加索的情妇。他还遇见了一个漂亮姑娘,跟她展开了一段甜蜜浪漫的爱恋。最终当他的心完全脱离现实,生活在“别处”之后,他抛开现实中的一切,毅然留在了黄金时代的巴黎。
《午夜巴黎》炮制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美梦,但又那么契合人心中真实的渴望。每一个在现实中倍感困顿的人,他们都在终日设想,如果有一天能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出走,到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去生活该有多好。于是,电影编剧就当了一回造梦师,为理想和现实的鸿沟架起了一道桥梁。现代人无不面临着生活压力和精神空虚的问题,他们丧失了激情和想象力,甚至丧失了幻想的勇气。电影编剧为大家制造了一个梦,即便早晚都会醒,虽是那短暂的出逃,却也能为一颗干涸的心注入新的能量。
这就是造梦师的魔力,能将现实的骨感变成梦想的丰满,能给人世的冰冷灌注情感的温度,它能让一个寂静的、没有一丝风的夜空洋洋洒洒飘落各色的花瓣,也能让一潭没有涟漪的死水出现海市蜃楼的倒影。
“讲述者”和“造梦师”的双重身份,对电影编剧来说,既是一次痛苦的人格分裂,也是一种奇妙的灵魂交融。希望更多年轻优秀的电影编剧,能够沿着这条艰险却风景怡人的路走下去,继续“观照现实”并“创造奇迹”吧。
(编辑:竹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