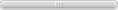你我同是,天上一抱云彩——余光中、朱炳仁、谢冕北大“《乡愁》会《云彩》”对谈

从左至右依次为余光中、谢冕、朱炳仁 韩沛奇 摄
4月20日,北京大学举办“诗与海峡”系列活动,不但举行了聘任台湾诗人余光中为驻校诗人的聘任仪式,铜雕艺术家朱炳仁诗集《云彩》新书发布及研讨会、“《乡愁》会《云彩》”对谈也同期举行。对谈会上,余光中、朱炳仁再叙盼望海峡两岸统一的心情,谢冕教授的总结更是精彩隽永:一抹天边的云彩,化解了两岸的乡愁。现将对谈整理摘编如下:
主持人:香港卫视副台长王明青
对谈嘉宾:台湾诗人余光中,铜雕艺术家、诗人朱炳仁,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、诗评家、教授谢冕
主持人:我们都知道40年前台湾诗人余光中老师一首《乡愁》在海峡两岸家喻户晓,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。”余老师绣口一吐,就影响了海峡两岸整整40年。40年后的今天,在我们杭州,在我们中国有一位这样的艺术家,他写下了《云彩》:“你落西湖三潭,我去日月双潭,西岸东岸,三潭双潭,你我同是天上一抱云彩。”两首诗把40年来海峡两岸从相隔相离相盼到相知相惜表达了出来。余老师,请您谈谈当时创作乡愁时的背景和台湾的文学状况。
余光中:乡愁这首诗大概是1970年代初,1971年,我写了好几首诗,都跟乡愁有关系,包括有一首是《乡愁四韵》,还有《民歌》。写《乡愁》我大概20分钟就写出来了,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大陆20年了,这种感觉在心里已经萦绕了20年,所以才能20分钟写出来。后来这首诗引起很多共鸣,收入教科书,远传到南洋,还有人谱成曲,王洛宾谱过,还有人谱成苏州评弹。
主持人:朱炳仁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工艺大师,进入诗歌界,也写了很多首诗歌。大家肯定有个问题想问而不敢问,那就是《云彩》的文学价值和现实价值能和余光中先生的《乡愁》相提并论吗?是作秀吗,炒作吗,是借乡愁完成从工艺界到诗歌界的华丽转身吗?这个问题我问朱老师,他说我可以回答,请朱老师说说您的心里话。
朱炳仁:一般都知道,诗歌是顶尖的语言艺术,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,文学爱好者都想写诗。我希望把艺术当做诗来做,把诗当做艺术来做,希望大家在我的铜雕作品中可以看出诗的情怀。写《云彩》的直接原因是我做了铜雕“同源桥”送到台湾去,桥的两壁正好刻着西湖三潭和日月双潭。我曾经五次到台湾,感受到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,想到这种强烈的家国不可分离的感受能不能用诗来表达?去年8月份到高雄,余老师和范老师两位专门在家中接待。余老师看到《云彩》后题了字:“两岸交流日,乡愁自解时;海峡有隔阻,不阻云彩飞。”诗歌更像是交流的桥梁,是有着深厚文化内容的桥梁,不管两岸之间怎样变幻起伏,永远都阻隔不了云彩的飞翔。我们的诗歌,就是要为两岸的交流两岸的和平作出贡献。这是我的幸运,也是艺术家的幸运,是海峡两岸追求和平、共同发展的幸运。
主持人:今天是余老师第二次来到北大现场,老师不光有乡愁,还有很多其他作品。我想您40年前写乡愁时的创作背景和文化交流情况跟40年后已经大不相同,比如老师去年在湖南秭归写下纪念屈原的《秭归祭屈原》,这些对文化交流和新诗创作会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和启迪,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余光中:乡愁并不是纯粹地域的阻隔,不只是同乡会的那种感情,乡愁还有时间的成分、历史的成分、文化的成分,这种乡愁是一种大乡愁。《乡愁》诗中先是母亲,再是新娘,再是大陆,都是女性的形象,逐步从小我提升为大我。我写过很多写给古人的诗,女娲、王昭君、史可法、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等等都写过,写那么多古人,也是一种仰慕,一种乡愁。
我回到大陆是在1992年,这20年间,我不能再写乡愁了,所以写了很多还乡、回乡的诗。比如写《重登中山陵》,我生于南京,上小学的时候跟着老师登中山陵,现在回来了,向孙中山报告。我登慕田峪长城,写了《登长城 访故宫》,又写了漓江,我父亲生在泉州,我又写泉州,都是还乡的诗。
主持人:余老师和朱老师分别是谢冕教授的旧友新知,请谢冕老师谈谈他跟余光中老师、朱炳仁老师之间的交往。
谢冕:余光中老师是我的老朋友,朱炳仁先生是我的新朋友。我和余先生的交往有一段时间了,他的一曲《乡愁》,我至今还感谢他。因为它传达的感伤也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我的家庭也是这样一个被隔成两半的家庭,我的父母临终没有见到我的亲二哥,1949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我的二哥生在大陆,热爱大陆,1949年到了台湾后,我的二哥最终选择了台湾作为他永久的家园。感谢余先生,他把我们很多普通家庭这种骨肉离散、盼望团圆的心情表达得那么好。
余先生不喜欢人家说他是乡愁诗人,我很赞同他的话,因为他的诗歌海阔天空,非常博大、宽广。我把余先生的诗编过一本书,余先生的诗太多了,对“情”有很重的期待和表达,包括乡情、亲情、友情各种各样的情感。
朱炳仁先生是我的新朋友,我看过朱炳仁先生的作品,铜看起来是那么冰冷,那么坚硬,到了朱先生手里变得那么柔软,那么温情,有节奏,有韵律,有情感,甚至表达出了人生的问题。铜雕里有他的人文主义情怀和真性情,而这种情怀,也是诗歌所需要的。朱炳仁先生在铜中发现了诗。我说一个故事,大家听一听。雷峰塔坍塌之后,由朱先生组建的一个团队建造新塔,朱先生负责雷峰塔的铜工艺。特别有趣的是,当时朱先生听从金庸先生的建议,认为让白娘子压在塔下太痛苦,所以新的塔是开放的,白娘子这样一位美丽、贤惠、勇敢无畏的女性能够自由回家。所以朱先生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表达人性的美好。
今天两位先生来北大,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达,就是—— 一抹天边的云彩,化解了缠绵的乡愁。 (本报记者何瑞涓整理)
(编辑:伟伟)